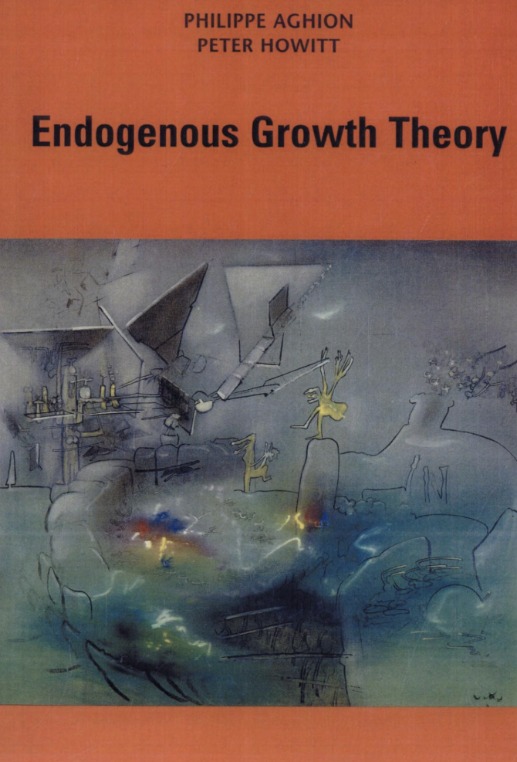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经济低迷中探索内生增长动力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三位学者,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两位美国学者,一位英国学者,都是这个领域杰出的代表人物。
在笔者2000年回国之前,当时师弟师妹们都在热衷地学习阿吉翁和豪伊特教授合著的内生增长理论教材。当时的经济背景主要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1999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的崩盘,全球经济增长也出现较长时间的疲软,世界经济的繁荣如何再起成为各国共同关心的话题。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要素投入边际收益率递减的“天然约束”,而是从熊彼特“破坏性创新的经济增长”的新视角去探索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可能产生的阻力,尽管后来的现实情况是全球化价值链的合作模式先带动了全球经济总需求的复苏,然后再进一步推动了创新成果的溢出效应。
这个理论让世界意识到,除了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外部重要性,也要重视教育、金融、知识传播和激励机制等无形资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所带来的颠覆性转变,这就是内生增长理论的魅力所在。今天,我们依然处在可能比上个世纪90年代更为严重的结构失衡的全球经济环境中。现在世界经济面临的长期增长低迷不是来自于经济周期的波动,所以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做法和关税举措反而抑制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虽然“创造性破坏”的内生增长驱动要素有时存在双刃剑问题,但是只要处理好这种两面性,营造出内生经济增长软实力的驱动力,那么,这种“破旧”释放出的被占有的宝贵资源和资源配置低效率模式的退出所带来的“立新”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其负的外部性,这可能就是当下解决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当务之急所需要建立起来的一种正确理念和行动方案。另外,这次他们的获奖对于中国而言存在一种特殊意义,那就是他们一直高度关注中国经济的增长,通过密切与中国相关机构开展学术交流,去努力探索他们的研究框架中对中国发展有建设意义的元素。下面笔者将从几个方面来整理他们的学术贡献及其社会影响。
内生增长理论具有时代意义
我们可以从三位的研究问题和视角来感受他们研究成果的时代意义。
首先是美国学者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他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观察知识与制度在长期增长中的作用(尤其是对技术变迁、工业革命起源的因素考证)。他的研究提出 “知识解释”工业革命:强调英国工业革命源于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的变革,尤其是实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积累、编纂与扩散,而不仅是资本积累或制度单一因素。这个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与去年诺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的“制度因素对发展的制约”的诠释形成了一定反差。他的研究成果还释放出这样的主张:观念、文化、学术共同体(如学会、工匠网络)这样的启蒙运动与包容性文化塑造了求真、实验和实用主义的知识生态。他的研究方法也表明,研究社会问题不能仅为了聚焦问题求得数理上的认证而牺牲现实多个因素交错的内生动力。他是将经济史与思想史、科学史结合在一起,强调非计量证据与“制度—文化”机制;这种研究方式对产业组织、创新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生重要的跨学科影响。
再来介绍一下菲利普·阿吉翁 (Philippe Aghion)的研究成果。他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熊彼特式内生增长模型”(Aghion & Howitt, 1992):以“创造性破坏”为引擎,质量爬升式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旧技术被新技术淘汰。把创新激励、市场结构与增长内生化,强调垄断租与竞争的双重作用。这就是他发现的倒U型关系(即“竞争促进创新”一个最优的度的把握问题):适度竞争提高“逃逸竞争”式创新激励,但过强竞争削弱租的回收、过弱竞争削弱追赶动机,都会形成创新激励的扭曲效应。今天我们重视“反内卷”和提高开放度、发挥“鲶鱼效应”的创新激励都是这种智慧的体现。
为此,如何能够创造一个包括创新驱动要素在内的经济增长新格局,就需要重视制度与增长之间内生互动关系:即要重视产权、金融发展、教育、人力资本、国家能力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互补性;具体要反映在与之配套的“适配性增长政策”(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中。当然内生增长存在的负外部性在于它会带来不平等再分配的收入效应:即创新驱动的增长会带来“破坏性”(传统产业被替代)——机会和收入向先发优势的创新行业倾斜,由此会带来一定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如果能够通过教育、社会保障与竞争政策的及时构建,那么这种暂时性的不平等现象就可能被包容性增长所化解。
阿吉翁的学术价值就是把熊彼特的观点严格建模并与实证体系对接,这套方法和理论体系已经成为现代增长理论与产业组织—创新交叉领域的主流框架。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与阿吉翁教授共同奠基熊彼特式增长框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将金融摩擦、市场结构、错配的市场摩擦导入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以此进一步探讨信贷约束、知识扩散、制度质量对创新的影响。他和·阿吉翁教授合著的内生增长理论这本教科书(译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一代研究者的建模训练影响深远。
总之,他们三人都聚焦共同的主题:“创新—知识”视为长期增长的核心引擎,但视角不同。莫克尔教授关注历史与文化—知识生态的长期演化,由此解释创新为何能持续发生。而阿吉翁教授和豪伊特教授则聚焦微观激励—市场结构—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诠释它们如何在当下和跨期内生地决定创新强度与方向。这次诺奖颁给他们三人很大原因是在于他们研究成果的互补性:莫克尔教授提供“深根”(观念、文化、社群与制度演化),而阿吉翁教授和豪伊特教授提供“机制”(竞争、知识产权、研发激励、创造性破坏)。将他们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就有助于设计既重视激励也重视知识扩散与开放科学文化的创新政策。
为此,他们研究的政策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应建立兼顾激励与扩散的创新制度组合:适度竞争、合理专利期限与范围、研发税收激励、开放标准与数据共享。二是应强化知识生态与人力资本: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科研资助体系、学术共同体与行业协会、科学传播与出版规范。三是应因地制宜的产业与绿色政策:对前沿经济体与追赶经济体采用差异化工具;通过碳价与绿色研发补贴引导方向性技术变革。四是要探索包容性增长配套的体系:再分配、流动性保障、再培训,缓解创造性破坏带来的短期失业与不平等问题。
诺奖评选更加重视实践意义
从今年诺奖评委在大量候选人中选择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三位代表者,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三人研究成果带来的现实意义的重视。具体反映在以下方面。
首先,创新驱动与生产率放缓的对症框架。众所周知,当今多数发达经济体经历生产率增长放缓(OECD与Penn World Table均显示2005年后TFP增速明显低于1990年代)。阿吉翁教授和豪伊特教授的熊彼特式增长框架把“创新速度、进入/退出、竞争强度、知识产权与人力资本”与长期生产率直接挂钩,为决策者(尤其是想靠高关税政策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而效果却恰恰相反的决策者)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药方(竞争政策、IP校准、研发补贴、教育结构)。另外,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推动绿色转型与方向性技术变革的增长要素至关重要。阿吉翁教授等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强调“价格信号+研发支持”可将创新从“脏技术”转向“清洁技术”,在碳中和目标与产业政策回潮的大背景下,具有高度现实性。
其次,把握好地缘政治与知识生态的韧性关系。在这个方面莫克尔教授关于“有用知识”生产—扩散体系、启蒙式开放科学文化与学术共同体的长期作用,为应对知识碎片化、与科技国际竞争的挑战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镜鉴——开放交流、标准化与职业共同体是持续创新的关键公共品。
第三,包容性增长与结构性转型的必要性。阿吉翁教授等关于“竞争—创新—不平等”的分析提示配套的教育、社保与劳动力再培训是将创新红利转化为广泛福祉的必要条件。当然,至于他们的观点是否具有超越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普遍性特征,确实需要更多的研究加以论证。
如美国与北欧存在差异:美国在1990年代反垄断较为强势、风险资本体系发达,配合高等教育与科研资助,符合“适度竞争+雄厚研发”的条件,支撑了IT革命与专利活动高涨;但2010年代后产业集中度与大平台网络效应增强,可能落在倒U型右侧风险区,解释了部分创新扩散放缓与市场活力下降的担忧。北欧国家(丹麦、瑞典、芬兰)在强竞争政策与高研发投入(GERD/GDP>3%)下,保持较高专利密度与全要素生产率(OECD MSTI与EUROSTAT可核)。而欧盟市场整合与竞争政策较强,但资本市场碎片化、规模化创业融资不足,导致“前沿逃逸”动力不如美国。
阿吉翁教授等关于资本市场深度与创新的研究提示,金融发展不足会抑制高不确定性研发投资。而在对新兴经济体(印度、东盟)的研究案例中,他们关注到这些经济体近年准入放宽与基础设施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进入,但阿吉翁教授等关于制度/金融发展互补的结论意味着:只有在金融可得性与法治改善同步的条件下,竞争冲击才更可能转化为创新与生产率提升。
同样,在绿色创新的方向性与政策组合上,他们的研究关注到欧盟早期引入碳交易与严格排放标准,汽车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清洁专利占比显著上升,阿吉翁教授的证据支持欧盟在绿色前沿维持竞争力的路径。而针对美国的情况,即联邦层面碳价缺位但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给予强力补贴与税收抵免,形成“研发+需求拉动”的另一种组合。这同样可促进清洁创新,但长期稳态仍受碳价预期影响。对于资源依赖型经济体,阿吉翁教授等的研究成果则主张:若缺乏明确碳价/标准,绿专利占比提升较慢,易陷入旧路径;政策应以收入中性方式引入碳税并回补低收入群体。
另外,在知识生态、历史条件与长期增长韧性之间的关系上,英美与北欧是一种开放科学、同行评审、学术—产业界互通、标准组织活跃的生态,与莫克尔教授所强调的“有用知识生态”契合,降低了创新交易成本,提高了扩散速度,支撑长期韧性。而对于欧盟与东亚的情况,他们发现这些经济体强调理工教育与国家研发投入,形成高强度“编码知识”生产,但若数据开放、学术流动、产学协同不足,则会削弱知识扩散与再利用效率。沿着莫基尔视角,这些经济体改革的着力点应放在开放科学、技术标准与职业共同体治理上。针对新兴经济体,他们的研究认为这些国家应建立工程师与技师的职业社群、标准化与中等教育普及,这对于把“进口技术”转化为本土持续改进至关重要。这些发现对于中国创新生态的优化提供了多元化选择的思路。
内生增长理论的学术价值
下面笔者将从“传统增长理vs. 内生增长(尤其是Aghion-Howitt)”的对比入手,分层梳理其创新点,并补充Mokyr在机制上的独到之处。
一是技术进步的来源:外生 vs 内生的特点上差异。传统(Solow-Swan,1956)技术进步A(t)通常外生给定;长期人均增长率由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决定。资本报酬递减,靠资本积累无法支撑长期增长。与此相对应的是阿吉翁教授与豪伊特教授构建的内生增长理论(Aghion-Howitt,1992)则将技术进步由企业的研发决策内生产生:创新投入→新技术出现→生产率提升。同时也包括创新激励的内生因素,它取决于市场结构、知识产权、竞争强度、人力资本与金融条件等政策变量。
二是创新过程的性质:平滑积累vs创造性破坏。传统理论技术作为“公共外生因子”,没有明确的企业进入退出与专利垄断的外部性特征。而内生(熊彼特式)增长理论则通过质量台阶(quality-ladder)机制揭示出:每次创新带来离散的质量/效率跃升;新技术取代旧技术,老垄断的利润被“破坏”,新创新者获得暂时“垄断租”(创造性破坏)。同时指出长期增长的推动要素是来自一轮轮创新与淘汰的动态过程。
三是市场结构与政策的角色:旁观者vs增长的“杠杆”。传统理论认为税、补贴、竞争政策对长期人均增长率影响有限(影响水平,但不影响稳态增长率),因为增长由外生技术决定。而内生增长理论则把竞争强度、知识产权期限与范围、进入壁垒、研发补贴、教育与金融发展等因素关联起来,明确揭示其都会改变创新激励,从而影响长期增长率与增长的方向(例如绿色 vs. “脏”技术)。
四是异质性与前沿距离:代表性经济体 vs分层产业/前沿-追赶差异。 传统理论中代表性企业/行业设定为共同特征,较少强调企业异质性与产业分层。而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企业/行业的异质性与“前沿距离”:靠近前沿的企业更依赖“逃逸竞争”式创新;远离前沿的经济体更依赖模仿、引进与吸收能力。从而推导出政策的“适配性”:前沿与追赶国家需要不同的竞争、教育与产业政策组合。
五是技术变革的“方向性”方面。传统理论认为技术进步通常是无方向的“中性”外生漂移,而内生增长理论则强调创新可以被政策与价格信号引导(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指出碳价、标准、补贴能把研发从旧路径导向新路径(如从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影响产业结构与长期增长质量。中国发展的很多相关实践也验证了这样的特点。
总而言之,传统增长理论把技术视为“天外来物”,难以告诉我们“如何让技术更快、更好、更绿色地进步”;Aghion-Howitt的内生增长理论则把企业的研发、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与制度设计放进增长引擎,解释了“为什么”和“如何”促成持续创新,并给出可操作、可检验、可因地制宜的政策杠杆。莫基尔教授则从历史视角揭示了知识生态与文化如何使创新成为一种可持续的社会机制,补上了“创新为何会在某些时空持续发生”的根本之问。
诺奖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建言
这三位学者都和中国学者有着密切的交流经历。比如莫基尔教授曾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在2015年他曾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三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旨在促进统计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合作。又如2019年他应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汇丰经济讲堂邀请,发表了主题为“The Englishened English”的讲座。在2021年12月他又受邀参与“北京大学高端学术讲学计划”,在线发表了题为 “态度、能力与‘大繁荣’的起源” 以及 “工业革命之再思考” 的系列演讲。
同样,阿吉翁教授也和中国学术界有很深的交流关系。其中最正式、最核心的在华学术职位是就是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杰出访问教授”。杰出访问教授这个头衔通常授予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并与学院有实质性合作关系的学者,其级别和受重视程度往往高于一般的“客座教授”。他还多次访问北大发展研究院和上海交大高金学院。而霍伊特教授则是应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邹恒甫教授的邀请来进行学术交流的。虽然他性格内向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他却坦诚地在中国记者面前谈了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些看法。
根据笔者的归纳,他们主要在三个方向给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建言:一是提升竞争与创新激励;二是因地制宜的“前沿—追赶”政策组合;三是通过方向性政策推动绿色与高质量增长。具体如下:
一是强竞争但不过度垄断,提升创新激励(Aghion/Howitt)。他们建议的内涵是,在关键行业降低进入壁垒,强化并购审查与反垄断执法,避免“僵尸企业”占用资源;同时保持适度知识产权激励,避免“专利丛林”。在预期效果上,要提高“逃逸竞争型”研发,促进市场份额向高生产率企业重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前沿距离与政策适配(Aghion/Howitt)。他们建议的内涵是,靠近技术前沿的行业(如通信设备、动力电池、AI应用)应更强调竞争与原创研发;远离前沿或追赶型行业应注重吸收能力、技术引进与标准化推广。对中国而言,东部沿海地区与头部城市群(深圳、苏州、合肥等)更适合强化竞争与基础研究资助;中西部和传统制造带则应重在职业教育、工艺改良与扩散机制。
三是方向性技术变革与绿色转型(Aghion等)。他们建议的内涵是,通过碳价/排放标准、绿色信贷与政府采购,推动研发从“高排放老路径”转向“清洁技术”,抓住新赛道的先发优势。对中国而言,应在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储能与电力电子领域,将“标准+碳价+补贴”协同,持续把专利与人才流向清洁路线。
四是知识生态与开放科学文化(Mokyr)。他们建议的内涵是,建设工程师共同体、行业学会、标准化与可复现的技术手册体系,推动“有用知识”快速编码与扩散;鼓励开放、同行评议与跨学科协作文化。对中国而言,应考虑在先进制造与工艺改良(如高端数控、材料与工艺参数优化)中,建立跨企业的知识库、手册与试验标准,缩短从实验室到产线的迭代周期。
五是人力资本、科研资助与金融支持的协同(Aghion/Howitt/Mokyr)。他们建议的内涵是,应考虑稳定的基础研究资助与高等教育质量,叠加对高不确定性研发的股权/风险资本支持,缓解“短视融资”问题,并通过职业教育提高一线工艺技能。对中国而言,应考虑优化科研评估与激励(从“量”转“质与原创”)、扩大长期耐心资本供给(创投—产业基金联动),并提升职业教育与工程师培养质量。
总之,Aghion与Howitt教授提供了“竞争—创新—政策”的可检验框架,告诉我们如何通过竞争政策、IP与金融教育改革提升创新效率并实现绿色方向性变革;莫基尔教授则提醒我们,持续增长离不开“有用知识”的制度化与开放文化。三者的建议与研究,为中国如何从要素驱动迈向创新与绿色驱动的发展阶段,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作者要感谢“孙立坚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小组”所有成员给与的资料和观点的共享)
(来源:天天基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