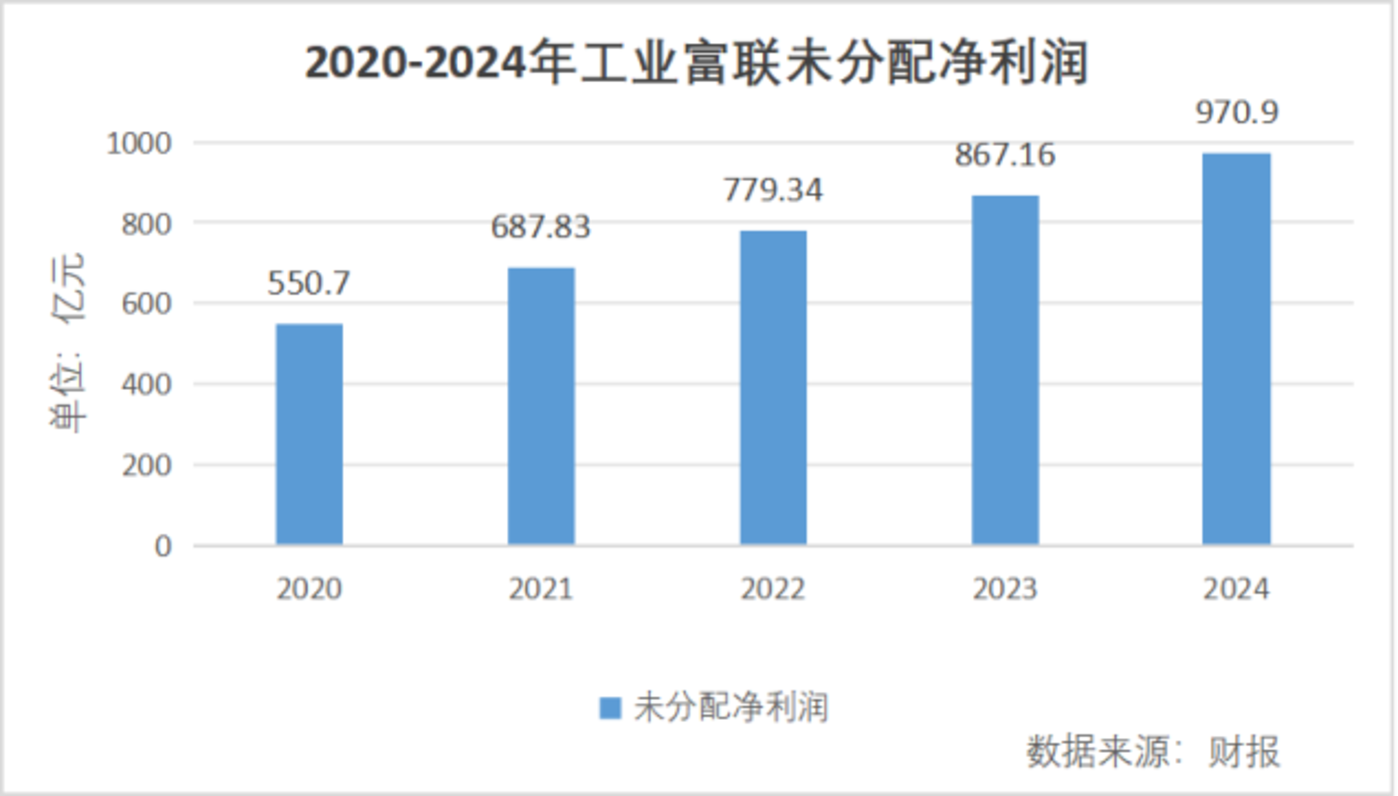娃哈哈失“宗”后,“娃”字辈竞争成焦点
文 |财观二姐
宗馥莉辞职后,搞笑的一幕来了。
先是亲叔叔宗泽后发朋友圈诉说宗馥莉德才不足,难担大任,后在宗馥莉推出新品牌娃小宗之际,宗泽后又宣布推出娃小智,势必要与其一较高下。
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就连品牌起名字也仅仅只是一字之差。
要说“娃小智”这一商业行为背后没有私人恩怨,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这也意味着,接下来娃哈哈与娃小宗、娃小智将在同一赛道竞争。
娃哈哈此前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竞争对手不再只是农夫山泉,而是自己的原董事长与创始人的弟弟。
果然,坚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开始瓦解。
事到如今,面对这场以宗家遗产争夺为导火索的商业内战,娃哈哈已经损失太多了。
迄今为止,娃哈哈失去了什么?
娃哈哈在宗庆后带领下,从草莽时代拼杀到如今的辉煌,成为凝聚中国一代人情感记忆的国货品牌。
但眼看起高楼,眼看楼塌了。
短短一年时间,娃哈哈经历工人维权,内部管理动荡,品牌信任动摇,以及如今的董事长辞职。
更绝的是,由于娃哈哈长期推进品牌改革,其真正的核心业务早已深度绑定在几大“内部派系”身上,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宗馥莉掌控的“宏胜系”。
宏胜不仅负责娃哈哈的生产,还几乎包揽了所有配套环节。也正因如此,宗馥莉在辞职董事长后,才有底气打造新品牌“娃小宗”。
据悉,宏胜系此前承担了娃哈哈约三分之一的产能,其代工的AD钙奶、营养快线等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六成。
尽管娃哈哈在自建基地去弥补功课,比如西安、成都工厂相继投产,不过2025上半年仍不得不让今麦郎代工,品控翻车、信任危机接连引爆热搜。
更重要的是,宏胜系把2 000多名技术大拿和供应链“老法师”打包带走,留给娃哈哈的所剩不多,就算新厂机器转起来,没有这批行业精英,想爬满设计产能,时间成本也将以“年”为单位计算。
在渠道上,娃哈哈同样依赖宏胜系。
2024年起,娃哈哈经销体系历经多轮调整:4月,宗馥莉要求销售公司骨干与管理层改与宏胜签劳动合同;10月,部分经销商被取消资格;11月,14个区域经销商协议换签。
最终,2025销售年度,西藏、青海两省经销商转由拉萨宏胜销售公司合作,黑龙江、吉林、辽东等共12个市场经销商转由杭州宏胜销售公司合作。
根据南方周末信息透露,目前90%以上的娃哈哈系列产品的经销均由宏胜系负责。
可以说,宗馥莉一走了之,宏胜系若彻底剥离,等于直接伤到娃哈哈的“利润主动脉”,接下来利润有可能“跳水式”塌方。
不过,娃哈哈最值钱的就是商标,价值大约900亿,这一核心资产还在娃哈哈手中。
其背后代表的是娃哈哈几十年如一日的口碑沉淀。
宗馥莉离职导火索就是商标使用权博弈。
使用“娃哈哈”商标必须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宗馥莉无法单独使用。
这也是为什么宗馥莉不得不另起炉灶,注册“娃小宗”商标的原因。
此外,宗泽后在宗馥莉离职这一敏感时间点推出“娃小智”,也可能看准了时机,借助这波热度来扩大品牌影响。
其招商人员更是表示,娃小智产品线包含AD钙奶、矿泉水、椰子水、八宝粥等,全面对标娃哈哈产品,价格甚至比娃哈哈还便宜。
说白了,“娃小宗”“娃小智”这些名字,就是贴着“娃哈哈”的品牌蹭出来的“亲戚”。
消费者一眼看过去,很容易把它们当成娃哈哈的“亲儿子”,很难分得清谁是谁?
满货架的“葫芦娃”们一拥而上,娃哈哈原本独一份的脸谱被撕成好多张,越看越模糊,娃哈哈品牌价值正在被稀释。
按照巴菲特的理论,快消品最硬的护城河就是品牌效应。
就像把依云和娃哈哈倒进玻璃杯里,舌头可能分不出高低,但大脑就是肯为依云多付那几倍差价——这就是差异化认知构成的品牌效应。
如今“山寨娃”们成群结队,护城河的水位正被一点点放掉。
现在娃哈哈品牌价值还值900亿,经历这档子事儿之后,有可能成为历史高点。
这场内战,对娃哈哈造成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几十年积累的品牌价值正在流失。
此前中国商业也有着相似案例,像加多宝与王老吉,十年了,仍在围绕商标争执不休。
最终消费者早已对“谁才是王老吉”失去兴趣,转而选择柠檬茶、气泡水等新品类,品牌情感价值被法律战消耗殆尽,迎来了双输的局面。
对于公司来讲,内斗哪有赢家?
娃哈哈品牌价值流失,宗馥莉就能如愿以偿把娃小宗带到娃哈哈的高度吗?
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输了面子,也输了里子,让利给原本的竞争对手。
农夫山泉与钟睒睒在宗庆后去世后,遭遇到前所未有谣言与网络攻击,农夫山泉业绩也一度由此受到阴影。
如今也算上演商业版的“天道轮回”,娃哈哈内斗不止,这为农夫山泉进一步扩张市场份额提供了机会。
去年春末,农夫山泉便携绿瓶纯净水突然杀向娃哈哈腹地,部分终端甚至把价格压到0.66元/瓶,通过低价直切对方基本盘,如今娃哈哈内斗不止,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
这也印证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家和万事兴,和气才能生财”。
宗馥莉辞职,背后是理念的偏差?
造成娃哈哈如今的局面,肯定无法绕开宗馥莉这个关键人。
不过也绕不开宗庆后为其留下来接班困境。
在宗泽后时期的娃哈哈,公司管理是典型的“家长制”范本。
娃哈哈甚至没有副总裁,大小事务基本上都归宗泽后管;
公司也没有严格的财务预算,用钱需要向上打报告;靠“家文化”情分留住元老,决策快但极度依赖宗庆后的个人经验;
而且宗庆后向娃哈哈员工承诺不裁撤45岁以上的员工,在员工中也有着强大影响力。
以此产生整个公司上下围绕宗庆后运作的管理方式,但这种家长式管理非常依赖个人威望以及对中国人情世故的理解。
不过宗馥莉从小就赴美留学,学得是西方那套现代公司管理流程,更信奉公司制度化、标准化。
就像宗馥莉在此前接受采访说,她希望用职业经理人来做公司管理,不希望公司创始人等于形象代言人。
可以看出宗馥莉和宗庆后的管理理念基本上相悖而行。
理念的相悖在宗馥莉彻底接手娃哈哈后,转化为内部矛盾的爆发。
2024年8月正式接掌娃哈哈后,宗馥莉上来就采取激进方式,想要把公司从“重人情”调整为“重制度”,但公司内部利益的平衡就是靠人情维系的,调整意味着平衡被打破,冲突自然而然出现。
比如把6000名员工劳动合同整体转签至宏胜饮料,同时取消沿用多年的“干股”分红。
但一纸变动触动老臣利益,53名退休职工联手起诉她和集团,要求法院判令股权回购无效,改革瞬间变成维权风暴。
同时宗馥莉在架构重组中把部分元老边缘化,引发反弹。
宗庆后堂弟宗伟拒绝并入宏胜,另创“沪小娃”;多地厂长与销售骨干因利益收缩而暗生不满,一位退休高管更公开质疑,内部出现罕见杂音。
去年宗馥莉通过辞职“以退为进”,让内部不得不为其妥协。
但别忘了,宗馥莉之所以能够“以退为进”,也是因为宗庆后刚刚去世,个人威望还在,消费者当时对宗庆后有着强烈的情感认同,这是内部妥协的市场基础。
甚至说,宗馥莉当时能“以退为进”也是因为父亲的人情所在。
但如今随着宗庆后被曝光有私生子,个人威望如今在消费者心中荡然无存,甚至娃哈哈品牌也受到重要影响。
宗馥莉个人威望在内部也没完全建立,改革自然越来越难以维系。
对于此时宗馥莉而言,“金蝉脱壳”或许是实现商业理想抱负的最好办法。
但是娃哈哈有着国资背景,最大股东是杭州国资委,并不是宗家的一言堂。
而宗馥莉距离脱壳成功就差个商标授权,但这也是最难的一步,商标作为娃哈哈核心资产,股东们不可能让步。
2024年底,国资股东以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第43条为依据,否决了宗馥莉授权宏胜系使用“娃哈哈”商标的提议。
如今又再次因为商标缘由,宗馥莉直接选择了辞职,进行自主创业,直接从“接班人”转化为“创业者”。
只是可惜的是,宗庆后多年来培养宗馥莉成为接班人,最终宗馥莉没有按照他的心愿走下去。
宗庆后曾说过,“娃哈哈是我的整个人生,所有的梦,一切的意义、价值、标签和符号。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证明。”
但这并不是宗馥莉的梦,宗馥莉的追求或许与宗庆后起初就不相同。
这场风波背后再度抛出了一个经典命题:当家族企业的代际接力棒从“创一代”移至“继二代”手中,两代人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坐标往往已悄然错位,于是,治理传承的悖论被赤裸揭开:究竟应由父辈的图腾式权威让位于子代的制度重构,还是子代的改革冲动必须向父辈的精神遗产俯首?
(来源:钛媒体)